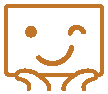摘要: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荀子和韩非为代表先秦诸子一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和总结了关注现世、肯定人在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及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思想中又难以避免地掺杂着神化思维的成分。“事在人为”与“秉承天命”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共存于他们的思想体系之中。
关键词:孔子;荀子;韩非;人化思维;神化思维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2
春秋战国时期,注重现实、注重人的生存状况、注重社会治理等内容及其价值取向成了这一时期思维模式的基调,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孔子、荀子、韩非无不如此。然而在人化思维的基调上,又掺和进不怎么协调的神化思维余音,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思维模式的基本特征。
一、 神化残余的存在空间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所拥有的解释外部世界、征服外部世界的能力远不足以摆脱神化思维的羁绊,更不可能超越于鬼神、天命之上。
1、在知识的积累和认识能力提高的基础上,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产生了有着唯物论色彩的“阴阳八卦说”、“五行说”,之后又出现了解释宇宙生成的“气”本原说,它们打破了神创论,促进了人化思维的形成和无神论观念的产生。但受知识和认识能力的限制,这些学说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释自然现象及其运动,人们对自然现象及其运动的困惑和无奈给神化残余留有存在的空间。
2、在社会政治方面,殷商、西周时期的神权随着政权更替受到普遍的怀疑,西周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地位岌岌可危,不堪一击,在现实生活的冲刷下,神化思维发生嬗变。但周天子神权的破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权观念破灭,而仅是一种转移,有人称之为神权下移。从社会政治角度来说,神化思维、神学观念仍有存在的土壤,它对春秋战国诸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3、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日趋瓦解,土地所有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演变成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剥削与被剥削并没有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发生根本性改变。处于社会底层受剥削的庶民百姓仍旧不得不盲目地接受命运的摆布,对苦不堪言的悲惨生活无法弄清其缘由,这种情况下,采取“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解脱内心的疑惑和苦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有限的科学知识积累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给神化思维、神学观念的继续存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春秋战国诸子思想中程度不同地存有神学内容,并用它们解释某些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人化思维:事在人为,人事在先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孔子、荀子、韩非,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和总结了关注现世、肯定人在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及决定性作用的思想。
1、 孔子说“为仁由已”
孔子通过对周礼虚假形式的批判,给礼注入新的内涵,“克已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用“仁”来充实礼,使礼能够表里如一。何为“仁”?据《论语》所载,孔子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的人有多种解释,从言谈举止到为人处事,道德修养都与“仁”相关。
我们现实中人如何去获得“仁”,如何去实践“仁”,在行为上达到“仁”的要求,进入“仁”的境界里去?在这个问题上,孔子提出了“为仁由已”(《论语?颜渊》)的命题。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到了一定境界之后,仁德难道离我们还远吗?我要它,它就来了。“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巳”(《礼记?仲尼燕居》)。
2、荀子论人定胜天
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天不是有意志的,不是能支配、主宰一切的神,而只是自然,只是自然的变化,所以,荀子反对关于自然变化的一切迷信看法。经过对“天”“神”的重新注释,剥去了人们以往披在它们之上的神秘性外衣,从根基上的动摇了神化思维存在的所谓“合理性”。
荀子人化思维所达到的辉煌顶点是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与其感叹、思慕自然,还不如去充分调动人事的力量,利用发展自然,为人服务。荀子充分肯定了自然界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其中闪耀着人化思维的光芒。
3、韩非论“治世之民,不与鬼神相害”
韩非在《饰邪》篇依据矛盾律原理指出了神化思维形式表现之一的卜筮的窘境和鬼神作用的不可信,龟神不可信。“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徵》)神化思维及其外化活动是国家衰亡的原因。“治世之民,不与鬼神相害,” (《韩非子?解老》)理想社会中人们不必与鬼神打交道。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韩非进一步发挥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论证人为的必要。自然界本无直箭、圆轮,它们的产生都是人们运用工具(“隐栝之道”)去改造自然物的结果。在社会历史发展问题,韩非认为是人的力量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引导社会进步的都是现实中的杰出人物,即“圣人”。而“圣人”之所以得以王天下,则离不开人民的拥戴,“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韩非子?饰邪》)圣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天命、鬼神意志的替身,离开了现实中的“众人”,也就一事无成。
三、神化思维:秉承天命,鬼神从之
孔子、荀子、韩非等人虽然在论述现实世界中的人在改造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中作用、肯定与自然界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等方面有明确的观点,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又难以避免地掺杂着神化思维的成分。
1、孔子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中孔子对“鬼”、“神”、“天”的谈论,虽然其中的一些严格说来不属于宗教观念范围,但也有一些则有着程度不等的宗教观念色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里的天是有意志,并能干涉人世间生活的存在。“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自称秉承天命,继承了周文王创造的斯文,因为有天意在身,有老天的保佑,所以身处困境被匡人围困,也不必恐惧惊慌。
至于孔子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把能安排人间生活,有着强力意志的“天”列为君子三畏之首,其对天的畏惧清晰可见。孔子于“仁”、“礼”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沿用天、鬼、神等宗教观念、试图借此解除人们内心的某些困惑,如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中的客观规律;圣人君人的由来;父母祖先逝去后的存在等。
2、荀子的“神道设教”
荀子在高举人定胜天旗帜的同时,把许多无法解释的疑问、困惑交给了神学,试图从中得到解脱,以求思想体系的圆满。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齐均。”(《荀子? 赋》)这个皇天实在是让人捉摸不定了,只是凡夫俗子们无法把握,只好听从它的安排。
正因为神有如此法道,人们对神就应保持敬重。此时荀子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主张“制天命以用之”,反对宗教迷信;一方面给皇天以造物主地位,认为“神道设教”有好处,“祭祀,敬事其神也。”(《荀子?礼论》)祭祀活动也是必需的,因为“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颇有点利用宗教迷信愚弄百姓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荀子的宗教意识观念有着明显的阶级烙印,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3、韩非的“因天命,持大体”
韩非改换老子“道”概念的属性,把原本是说明自然界万事万物本源的道改换成社会现象的“是非之纪也”。老子的道本身就已是神秘的东西了,把它引入社会生活领域使世俗生活的本源也不可避免地神秘化。
韩非虽没有直言“皇天隆物”之类极其明显的神学语言,而是用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无法证实的“道”说明所谓明主权威的来源。“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日明主。”(《韩非子?功名》)因而明主能够“因天命,持大体。”(《韩非子?大体》)也许韩非的本意并非想重蹈君权神授的覆辙,但最终还是未能摆脱神学传统观念的影响。
从上述孔子、荀子、韩非思想中残存的神学思维及其天命、鬼神观念来看,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宗教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它的影响仍在,远远没有消除。
四、人化神化的媾合
春秋战国思想文化中神化思维与人化思维,有神论与无神论混合交织在一起,在亦人亦神的平衡中形成了“人事在先,鬼神相随”的奇特文化现象。
1、人学神学的媾合使得春秋战国思想文化中的宗教神学观念过分政治化。春秋战国诸子不是神学家,他们的宗教神学观念不是为了神学而神学,是为了弥补自身思想理论中的缺陷。春秋战国诸子在理论上需要说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君主的绝对地位何以得到?对于这个问题,春秋战国思想家虽然想在世俗生活中寻找答案,但都未能如愿,最后只得在神学范围里去想象虚构,以摆脱思想中的困惑。特别是荀子、韩非用“皇天”和神学化了的“道”来证明君主地位的合法性,形成了一道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景观。荀子、韩非为政治神学的始作俑者,如果说他们与夏、商、西周的王权神授观念有何异同的话,可以认为本质上一致,理论自觉性不同。
2、就思想体系内容逻辑一致性要求来看,人学神学的媾和使春秋战国思想文化形成了又一道明显的悖论:一方是坚持“事在人为”原则,“没有救世主,鬼神与现实生活无涉。另一方面是春秋战国诸子又大多把治理社会、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圣人、君子、贤人身上。这些人何以能担此重任,“秉承天命”的解释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则成了最简单而又最“合理”的选择了,也就是说存在着能普渡众生救人民于苦难之中的救世主,神通过它的代表来干预现实生活。双方的对立明白无误,却又溶于一体,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
3、人学神学的媾合使得春秋战国诸子学说出现构造上的断裂层,人学神学的并存,造成理论体系内部无法融合贯通起来,这一点在韩非的学说中尤为明显。从人学角度来说,作为君主自然应利用其地位,以驾驭臣下和百姓,此时的君主是完全世俗化了的君主。从神学角度来看,君主又是秉承“道”的旨意来统治世俗社会的, “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定也,令事自定也。”(《韩非子?五道》)此时的君主已失去了世俗意义,被神化了,所以“君无见其所欲”,要“去好去恶”,“去旧去智。”(《韩非子?五道》)成了一个超凡脱俗抽象人。同样一个君主,两付不同的
面孔,在转换过程中缺乏一个合理的铺垫,也就被割裂了开来。
总之,在春秋战国时期,人化思维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成了这一时期乃至后世思维模式的主旋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限制,使神化思维和天命、上帝、鬼神等宗教观念并没有真正退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舞台,它们既使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化思维和无神论思想黯淡了许多,又使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陷入了一道深深的悖论之中。
参考文献
[1]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
[2]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 儒家思想的根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
[3]丁祯彦等:《春秋战国时期观念与思维方式变革》,湖南出版社,1993年
【孔子荀子和韩非思维模式共同特征探讨】相关文章: